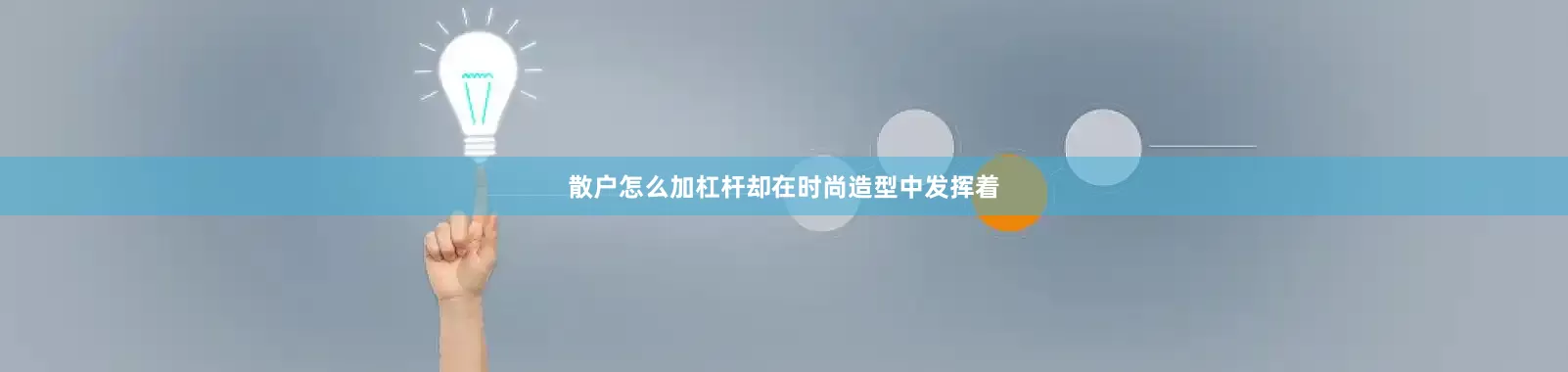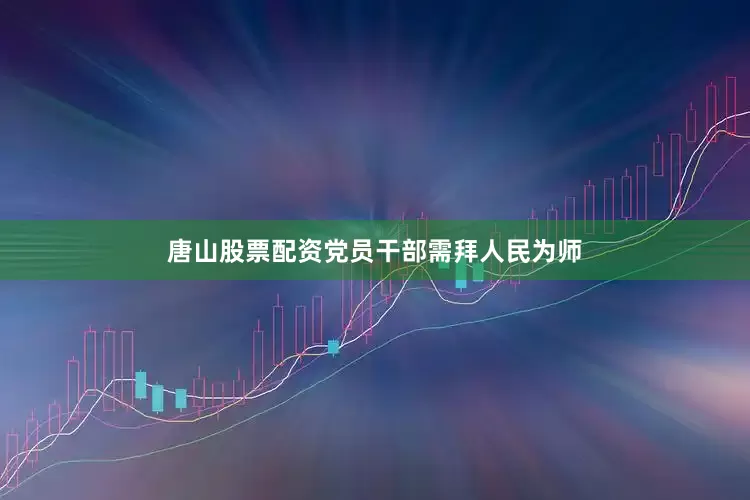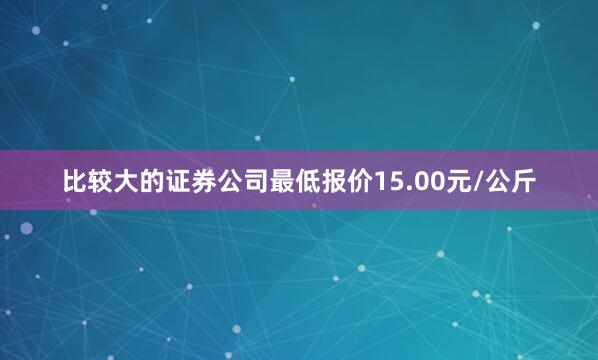图片
2025大吉
NEW YEAR
图片
图片
图片
真正的功夫修炼,不仅需要外在的努力,更需要内在的领悟。只有将“求”与“悟”结合起来,才能达到功夫的至臻境界。无论是学习、工作还是生活,在勤奋努力的同时,更要注重内心的觉醒和领悟!
图片
关注武宗
学
天下武功
图片
图片
养派生 食补胜药补·练功百病消
图片
图片
以武学打开世界·智者不匹夫 武者无懦夫
长生不老的秘诀,那得先从身体内部的根基说起。这身体就像一棵大树,根深才能叶茂。而中医里常说的肾,它可不只是管排尿那么简单,它可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,是精气神的总仓库。从头顶的泥丸宫,一直到尾骨的尾闾,这一整条中轴线都跟肾息息相关。所以,想谈养生、谈长生,绕不开肾这个核心。
咱们接着往下看,身体里还有个重要的地方叫膻中,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气海。这地方在两乳之间,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我们呼吸进去的气,主要在这里汇聚运行,然后分发到全身,调节阴阳平衡,可以说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来源。再往下,肺下面有个隔膜,像个幕布一样把胸腔和腹腔隔开,它的作用可不小,能挡住那些脏东西,不让它们污染咱们的上焦,也就是心肺这些娇嫩的器官。
这人体内部的能量,也就是元气,它可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跟着时辰走,就像大自然的节律一样。你看这12时辰,从子时开始,阳气生发于尾闾,然后临气、泰气、大壮气一路向上,到午时阳气冲到泥丸宫,这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。过了中午就开始往下走了,遁气、否气、观气、剥气、坤气,最后回到气海。这个过程就像一个能量的潮汐,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。了解这个规律,对咱们调养身体、把握时机很有帮助。
刚才提到了泥丸宫、黄庭丹田,这些都是身体里的关键穴位,或者说能量中心。古人把它们分成了前三关和后三关。前三关从上到下是泥丸宫,对应着我们的精神意识;黄庭,也就是心口窝,是中正安和的地方;还有下关水晶宫,就是我们常说的丹田气海,是能量的储存库。后三关是从下往上,尾闾是能量的起点,夹脊是能量提升的关键通道,玉枕则连接着头部和大脑。这六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能量循环系统。
说到祖窍,这可是个神秘的地方,据说是我们先天真性、天命所寄托之处。白天它藏在眼睛里,晚上就潜入肾脏里积蓄能量。脐轮就是肚脐周围,是生命的门户,象征着出生。两肾中间有个命门,非常重要,是人体能量的枢纽。脐下一点点,分别是下丹田和关元气海,都是储存精气的重要区域。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修炼内功、调养身心的关键所在。
除了刚才说的几个大穴,身体上还有很多细微的穴位,各有各的妙用。比如头顶的百会穴,古人叫须弥顶,上面有九宫,是沟通天地的要道;口是丹池,咽喉是十二重楼,是气机升降的通道;心口是绛宫,腰部是密户,肛门是谷道,前面还有玉泉穴。更有意思的是,古人还提到了知积石、鹊桥、银河、涌泉穴等等,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,也暗示了身体内部复杂的能量网络和信息传递系统。
刚才我们说了不少身体上的具体位置和功能,但有人可能会问了:“你说的这些难道就是大道的全部了吗?是不是还有更深奥的东西没说?”大道真是博大精深,难以穷尽,刚才说的不过是沧海一粟、管中窥豹罢了。要想真正理解大道,还得听听古人的智慧。
淮南子对道的描述真是气势恢宏,他说这道覆盖天地,包容四方,高不可攀,深不可测,它无形无相,却孕育万物,滋养一切。你看这描述:“植之而塞于天地,横之而弥于四海,舒卷自如,弱而能强,柔而能刚”,简直是无所不能。它生养万物却不占有,成就万物却不干预,这种无私奉献、自然而然的状态就是道的体现。“忽兮恍兮,不可为象”,这道太玄妙了,没法用具体的形象来描绘。
接下来是老子,他的《道德经》更是道家思想的源头。开篇就问: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什么意思?就是说你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,已经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;同样,你能给它起名字的,也不是真正的道。所以“无名,天地之始;有名,万物之母”,要体会道,就得“常无欲,以观其妙;常有欲,以观其徼”。这“无”和“有”看似对立,其实同出一源,都是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 。
老子还说,这道你看不见,叫“夷”;听不到,叫“希”;摸不着,叫“微”。这三者混在一起,就是“一”。它上面没有明亮,下面没有昏暗,连绵不断,无法命名,最终归于虚无,这就是“无状之状,无象之象”,恍惚不定。你迎着它,看不见它的头;跟着它,看不见它的尾。所以要想把握现在,就得遵循古老的法则,了解事物的本源,这才是道的精髓所在。
庄子的故事就更精彩了。南伯子葵看到女偊年纪轻轻却面色红润,就问他秘诀。女偊说:“我闻道矣。”南伯子葵想学,女偊却说:“你不是那块料。”为什么?因为“以有圣人之才,而无圣人之道;我有圣人之道,而无圣人之才”。这就好比有发动机没车,有车没发动机都不行。女偊接着说,她花了三天时间让对方能“外天下”,放下对世界的执着;七天后能“外物”,放下对物质的执着;九天后能“外生”,放下对生命本身的执着。达到这种状态,才能“朝彻”,看清事物的本质;“见独”,认识到独一无二的真理;最终达到“撄宁”,超越生死,进入一种宁静而充满生机的状态。
庄子还说,这道有情感、有信誉,但它本身是无为无形的,可以传授,但不能强求接受。它自本自根,存在于天地之前,贯穿于万物之中。从韦氏、伏羲到黄帝、颛顼与西王母,再到彭祖,这些传说中的圣贤帝王都是因为得道,才有了非凡的成就和长寿。你看这道的力量是如此强大,能让帝王将相、神仙鬼怪都为之倾倒。
庄子又讲了庚桑楚的故事。这位庚桑楚是老子的弟子,得了一部分老子之道,跑到北边的畏垒山住了下来。他不怎么说话,也不怎么干活,结果当地的人反而越来越富裕,日子越过越好。老百姓觉得这肯定是圣人,要给他建庙祭祀。庚桑楚一听心里很不爽,觉得弟子们太肤浅了。他说:“你们看春天和秋天,百草生长,万物成熟,难道是它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吗?是大道在运行,我这样做只是顺应大道,让百姓安居乐业,我怎么能居功自傲呢?”这就是治人的境界——不居功,不争名。
庄子还提到了曾子,就是孔子的学生曾参。他在魏国生活非常简朴,衣服破了补丁罗补丁,鞋子破了露着脚后跟,但他依然坚持唱歌,歌声响彻天地,金石为之共鸣,连天子诸侯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庄子借此说明,真正追求大道的人会忘掉自己的形体,忘掉利益的诱惑,最终达到“坐忘”的境界,也就是心无挂碍,彻底解脱。
关尹子,这位老子的老师,对道的理解也很有深度。他说道不是不能说,说不出的本身就是道;道也不是不能想,想不到的本身就是道。世间万物变化莫测,人事纷繁复杂,争论不休,就像瞎子摸象,各执一词。你试图用言语去描述它,就像吹口气瞬间就散了;你试图用思维去捕捉它,就像尘埃一样渺小。圣人的智慧也难以完全把握它,鬼神也无法完全认识它,所以道是不可为、不可治、不可测、不可分的。我们只能用“天命”“神”“玄”这些词来勉强形容它。合起来,就是“道”。
关尹子打了个比方,说他的道就像大海,你往里面扔金子、石头、垃圾,它都照单全收,视而不见;它能容纳小鱼小虾,也能承载巨鲸、大鲲。你往里加水,它不会溢出来;你往外分水,它也不会减少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道是包容万象、不偏不倚、不增不减的。他还说,天不能种莲花,春天不能种菊花,所以圣人不违背时节;洛阳的橘子不能种在汶水,所以圣人不违背习俗;圣人不能让手走路,不能让脚握拳,所以圣人不违背自己的特长;圣人不能让鱼飞,不能让鸟跑,所以圣人不违背别人的特长。总之,道就是灵活应变,不拘泥于形式,不被外物所束缚。
关尹子又说,狡猾的人能战胜贼人,勇敢的人能捕获老虎,关键在于什么?在于克制自己才能成就自己,在于懂得利用万物,才能更好地服务万物。最厉害的是什么?是能忘掉道,反而能拥有道。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,但仔细想想,当我们不再刻意追求,不再执着于某个目标时,反而可能更容易达到目标,或者发现真正的道。
他还说,谈论道就像谈论梦,梦里有金玉器皿,你能说出来,但能拿给你吗?听的人能听到,但能真正得到吗?只有善于倾听的人,不执着于字面意思,不陷入辩论,才能有所领悟。关尹子又用了一个盆和水的例子,你拿个盆当沼泽,拿块石头当岛屿,鱼在里面游来游去,感觉走了几万里路都不会累,为什么?因为水没有源头,也没有归宿,圣人之道也是如此,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,所以能够无限延伸,永不枯竭。
他还说,圣人之道看似简单,“节节彻彻,堂堂正正”,但又蕴含着无穷的奥秘,能与万物相通,又能超越万物。就像种子发芽,雌鸟孵蛋,看似自然而然,但背后是阴阳调和,精气凝聚的奥秘。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身体如同梦境,那么就可以驾驭精神,遨游太虚;认识到万物如同梦境,就可以凝聚精气,创造奇迹。这道既能让我们长寿,又能让我们超越生死。
关尹子还强调了修行的方法,他说少说话的人不容易被人记恨,少做事情的人不容易被人挑剔,少耍小聪明的人不容易让人劳累,少显露才能的人不容易被别人驱使。做事要真诚,行动要简洁,待人要宽容,回应要沉默,这样道就不会枯竭。他还提醒我们,做事情要先谋划,做决定要依据道理,具体执行要依靠他人,最终成功要归功于天。向现实学习,向古人学习,做事要借鉴他人,但道要靠自己领悟。金银珠宝难以舍弃,泥土石头容易丢弃。学道的人遇到一些高深的言论或奇特的行为要小心谨慎,不要轻易执着,执着于这些就像得了心病,很难治好。
不明白急务却去做那些繁杂、无关紧要甚至奇怪的事情,只会招来困顿和灾祸。要知道道无处不在,不能舍近求远、舍本逐末。
关尹子再次告诫,别听到别人说“宁寂”“遂身澄澈”“崆峒”“慧明”这些词就害怕退缩了,真正的道理往往超越了语言和概念,关键在于超越这些表面的描述去体会那微妙的意蕴。他还引用了天道的例子,说天覆盖万物,有生有杀,但天没有偏爱或厌恶;太阳照耀万物,有妖魔鬼怪,也有美女帅哥,但太阳没有厚此薄彼。圣人之道也是如此,是天命所赋予、是时势所契合、是人事所成就,而不是圣人自己能创造的。
所以,圣人不占有道、不占有德、不占有事。圣人知道没有“我”,所以用仁爱待人;知道事情没有“我”,所以用道义处事;知道内心没有“我”,所以用礼仪约束;知道知识没有“我”,所以用智慧判断;知道言语没有“我”,所以用诚信守诺。圣人之道灵活运用仁义礼智信,不拘泥于任何一种,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
关尹子继续说,不要以为圣人勤奋努力,道就是靠勤奋得来的;也不要以为圣人坚守原则,道就是靠坚持得来的。圣人的努力就像射箭,是借助弓箭的力量,而不是他自己发力;圣人的坚守就像握着弓箭,是顺应弓箭的特性,而不是自己硬撑。如果用言语、行为、学问、知识去追求道,那就像互相推诿,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智慧。就像泉水叮咚、鸟儿飞翔、相机拍照、计算梦境,都是自然而然的,不需要刻意去求,只要心念一动,道就会自然显现。用事物去建造东西很难,用道去抛弃事物很容易。天下万物,成之难,坏之易。心对应枣树,肝对应榆树,我与天地相通,随情绪变化,梦里是水;随情感变化,梦里是火。天地与我相通,我与天地似合似离,最终回归本真。
子华子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:善不可以有为。意思是说,真正的善不是通过刻意去做善事就能实现的。尧舜这样的圣王,他们问臣子“你怎么才能把我的事做得更好”,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,一种试图通过有为来达到善的尝试。子华子认为,这种上下争夺善的做法会导致双方都陷入实力的计较,无法达到真正的平和与公正,失去了这种平和与公正,尧舜也就不再是尧舜了。所以,真正的善不是靠有为,而是要回归到尧舜那种自然而然的状态,谨记他们的榜样,而不是刻意去模仿或超越。
杨雄这位西汉的大学者,他对文学和道的理解都很深刻。有人问他年轻时是否喜欢写赋,他承认是,但很快就说长大了就不该这样了。有人问赋能不能用来讽刺,他说讽刺可以,但如果不加节制就容易变成劝告,反而失去了讽刺的力量。他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华丽辞藻,认为那是“女工之蠹”玩意儿。真正的文章应该像宝剑一样能保护自己,对于那些辞藻华丽但内容淫靡的赋,他评价是“劝百讽一”。他认为孔子的门徒如果用这种方式,贾谊、司马相如这些人可能就进不了殿堂和内室了。他还强调辨别事物要看本质,就像看女人要看内在气质,看书要看是否符合法度,而不是只看外表。他甚至说舍弃舟船就想度过众多小河,舍弃五经就想寻求道,抛弃日常食物就想品尝异域珍馐都是不明智的。真正的道就像孔门一样是入门的门,但他自己却认为他有不通过门就能直接进入的境界。
杨朱主张贵己、重生、寡欲,他认为大道是广阔无边的,过去圣贤都曾探索过,但探索时过了头就失了“中”,达不到要求就不算成功,都不能弄虚作假。有人问道是什么,他说道就是通达,没有不通的地方。有人问道能不能走别的路,他说走到尧舜文王那里去是正道,走到其他地方去是旁门左道,君子应该走正道,不走邪路。有人问道像不像路上的车辙、河里的水流日夜不停地流淌,他说路虽然弯,但只要能通向中原就可以走;河虽然弯,但只要能流向大海就可以走。有人问事情是不是也这样,他回答是的,只要能通向圣贤的境界就可以走。
玄真子讲了一个故事,有两个修行人,一个叫观之君,一个叫通真之博。他们在讨论道德有无问题,争论了半天也没结果。观之君说:“我在官亭里知道道不是没有,而是能看见'有’;后来在望台上又知道道不是'有’,而是能知道'无’。”通真之博就说:“至道非有非无,只是你们的看法不同。”他打了个比方,说你看太阳和星星离你远近不同,大小也不同,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。你用远近来衡量大小,却忽略了温度;你用温度来衡量远近,就忽略了大小,所以没有远近之分,只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。道也是如此,你执着于“有”就只能看到“无”,你执着于“无”,只能看到“有”,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心在执着,道的本体并没有改变。所以争论道的有无就像争论太阳的远近一样,是执着于表象,没有触及本质。这两个修行人听了哑口无言,退下了。
达玄夫子评价说,这次辩论通过一个简单的三光远近问题,解决了关于道的有无之争,真是厉害。
尹文子说,大道是无形的,你看不见,但它从未离开过你;大道是无声的,你听不见,但它从未停止过运作。我们所说的可见可闻,不是指眼睛、耳朵能直接看到听到的,而是指用心去感受、用意去体会。就像刮大风,它能撼动山上的树木,掀起水面的波浪,难道能说它不存在吗?同样,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,难道就能说它没有吗?关键在于用心去感受,用意去领悟。
陆门子提出了一个非常辩证的问题,他说:天那么明亮,太阳明明挂在天上,为什么会有日食?大地那么稳固,高山屹立不倒,为什么会有山崩?夏天万物生长,为什么麦子会枯萎?冬天万物凋零,为什么松树反而茂盛?水明明是寒冷的,为什么汤谷会有温泉?火明明是炎热的,为什么萧山会有寒溪?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,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不去理解它们,这体现了道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。
南山子提出了一个修行者应有的姿态,他说:不要用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,也不要默默无闻地追求完美;不要声名显赫地逞强,也不要低声下气地隐藏。能不能做到纯粹专一,能不能断绝外界的诱惑,能不能像山一样屹立不动,又像海一样容纳万物?如果能做到这些,就可以说是接近道了。这强调的是内心的平和、坚定和开放。
恒通子从本源的角度来谈道,他说:太初是理的开始,太虚是气的开始,太素是形象的开始,太乙是术的开始,而太极则是理、气、象、术这四者的总源头。他还强调了语言的局限性,他说道是通过语言来传承的,但也可能因为语言而被堵塞。不是语言本身堵塞了道,而是我们理解错了。一旦理解错了,就变成了训诫,再错下去就变成了华丽的辞章,当语言变得繁盛的时候,道反而衰落了。所以学习的人不应该过分看重语言文字。
方叔子,也就是周敦颐的弟子,他从易经的角度来阐释道,他说:伏羲创立先天八卦是万古文化的源头,后来的文王、孔子等人发展了易经,但离圣人越来越远,精华被损耗了很多。直到周敦颐,才重新揭示了千年来被遗忘的秘密。太极就是这个秘密的核心,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这就是阴阳五行、万物产生的根源。太极体现在天地造化中,就是阴阳刚柔;体现在人心中,就是仁义礼智信。圣人能够把握太极的动静变化,所以能体悟到人道的精髓。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就是阐明这个道理的。后来朱熹继承并发扬了这个思想,使得太极之道更加清晰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可惜的是,后来有些人喜欢标新立异,反而偏离了正道。
临川子,也就是王安石,他强调学习道要循序渐进,他说:立志要高远,但功夫要从细微处做起。就像治水一样,要从下游开始疏通河道,哪怕是最小的沟渠也要清理干净,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达到大德的境界,也不能舍弃眼前的细节去追求遥远的目标。圣人教导人总是从最普通的话、最平常的事说起,循序渐进,非常实在。所以孔子很少谈论“性与天道”,因为这是很难用言语完全传达的。程颢、程颐兄弟把太极图藏起来,也是深思熟虑,因为他们知道要真正理解道,还得从孝悌礼乐这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入手。陈亮也说登高要从低处开始,远行要从近处开始,这是圣人教导的切实方法。可惜现在很多人读书只是为了增长谈资,写文章只是为了炫耀文采,这样下去想要改变自己的气质,恐怕很难了,更别说求道了。
阴阳子说:道离我们远吗?一点也不。只要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,用心去体会就能发现道的真谛。圣人离我们远吗?也不远,只要你亲身去体悟就能感受到圣人的境界。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放下凡俗的心。真正懂得道的人不需要别人开口,就已经明白了祖宗传下来的智慧;不懂道的人就算绞尽脑汁去思考,也只会对着山峰发呆,一无所获。这强调的是修行和体悟的重要性,而非空谈。
冉惠子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话来说明道,孔子说自己没有知识,颜回认为自己赶不上孔子,孟子说自己没有特别的才能。冉惠子认为,真正懂得道的人是不会把道据为己有的,那些认为自己掌握了道的人恰恰是不懂道的人。懂得道的人就像一个空空如也的鄙夫,因为他可以进入圣人的境界;懂得道的人又像一个赤子,因为他不需要学习,就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。这说明真正的道是谦逊、空灵、自然的。
阳明子,也就是王阳明,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见解。有人问他道可以言说吗,他说可以,但这个“有”是“未尝有也”;有人问道可以看见吗,他说可以,但这个“无”是“未尝无也”;有人问那怎么才能看见,他说通过“见而未尝见也”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真正的“有”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占有,真正的“无”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空无,真正的“见”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视觉。这是一种超越了有无、见不见的境界,是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。陷入“无”,心就无所用;执着于“有”,心就被无用的东西牵绊。只有在有无之间、在见与不见之间体悟微妙的境界,才是真正的“见道”。
甘明子探讨了天与道的关系,他说:天有没有开始?没有。如果说天有开始,那就是说道有开始,这就不对了;天有没有尽头?没有。如果说天有尽头,那就是说道有尽头,这也错了。天和道本来就是一体的,怎么能分开?我们整天看着天却看不到道,整天谈论道却不谈论天,都是糊涂。他批评了那些追求虚幻奇异事物的人,认为他们迷失了方向,就像追逐彩虹却忘记了脚下的路。他说:如果说道升了天,那天外面还有天吗?如果说道的根源在天,那天里面还有天吗?道和天本来就是一体的,怎么能用语言把它们分开呢?
明辽子强调了内心状态的重要性,他说: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道,那么无论身处何种环境,都能保持内心的安宁。道不在外面,而是存在于我们自身。如果内心能够应对外界的缘起而不受干扰,就不会产生障碍。所以得道的人即使身处喧嚣的闹市,内心也能像空灵的殿堂一样寂静;即使住在偏远的山林,“真性”也能充盈饱满,不会感到枯萎。相反,那些没有得道的人住在闹市里,就会产生各种杂念,心神不宁;住在空山里,又会想起尘世的喧嚣或者感到寂寞。这说明关键在于内心是否安住。
傅元子说:我们的道可以用一个“一”来贯穿。“一”既是中心,也是隐藏的,大的敦厚统合一体。太极是藏在用中的,贯穿就是和谐,是流露在外的;小得像溪流一样流淌,每个部分都包含着一个太极,是显现在仁爱中的。通过致知和精研易理来明了它,通过恢复礼仪来体现它。“道”没有隐藏的,因为这个道理没有隐藏之处;我想保持沉默,因为这个道理不容许言语。如果昧于此而失去它,或者窥探他而窃取他,就是“天贼”。这强调了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,以及对它的尊重和敬畏。
老子再次强调了清净的重要性,他说:大道是无形的,却能生养天地;大道是无情的,却能运行日月;大道是无名的,却能长养万物。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,勉强叫它道。道有清浊,有动静,天清地浊,天动地静;男人清,女人浊,男人动,女人静。清是浊的源头,动是静的基础。人如果能常常保持清静,就能与天地合一。可惜人的神喜欢安静,但心会扰乱它;人心喜欢安静,但欲望会牵引它。所以要能遣其欲,让心自然平静;澄其心,让神自然清明。这样六欲自然不生,三毒自然消灭。做不到这一点,是因为心不清、欲未除;能做到这一点,就要内观其心,心无其心;外观其形,形无其形;远观其物,物无其物。三者都悟透了,就只剩下空。观空也是空,无所空,所空既无,无无亦无,无既无就是湛然常寂,寂无所寂,欲望还能生出来吗?欲望不生,就是真静;应对外物就能真常;德性常应常静就能常清静。如此真静,渐渐就能进入真道,进入真道就叫做“得道”,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“得道”的,而是与万物化育。能悟道的人才能传承圣道。
老君,也就是老子,再次强调了不争不执的重要性。他说:上等的人不争斗,下等的人喜欢争斗;上等的德行不自以为有德,下等的德行执着于自己的德行。那些执着于道的人反而不能称为有道德。众生之所以得不到真正的道,就是因为有妄心。有了妄心就会惊扰自己的神,惊扰了神就会执着于外物,执着于外物就会产生贪求,有了贪求就是烦恼,有了烦恼就会忧愁痛苦,身心受损,遭受污浊,流浪于生死轮回,永远沉沦在苦海之中,永远失去真道。真正的常道要靠自己觉悟才能得到,觉悟了道的人才能常保清净。
关尹子再次强调了精神意的重要性,他说:果实要有种子,种子要靠水、火、土才能生长,这三者具备了生命才能生生不息。如果缺少了水、火、土,就像大旱、洪涝、贫瘠的土地都无法生长。人的“金、水、神、火、意土”也是如此,它们本来是分离的,只有通过修炼把它们合在一起,才能在体内产生奇妙的变化,就像巫师能从虚无中变出很多东西一样。他还说:魂是木,根在冬天的水,花在夏天的火,所以人的魂藏在夜晚的精气中,显现于白天的精神。魂与神结合,所以能看到“我”,独自存在,因为精气本身没有“我”;魂与神结合,所以能看到“人”,因为神本身没有“我”。认识到身体如同梦境,身体随情感变化就可以让精神飞升,成为“我”遨游于太虚;认识到万物如同梦境,万物随形态变化就可以凝聚精气,创造万物,驰骋于天地之间,这就是道。能认识到精神就能长寿,能忘掉精神,就能超越生死。息气养精就像金属生水,息风养神就像木生火,这是借助外物来延长精神;树水养精,精气就不会枯竭,摩擦生火养神,精神就不会枯竭,这是借助内功来延长精神。至于忘掉精神而超越生死,我之前已经说过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51配资网-股票配资安全的平台-炒股配资配资官网-石家庄股票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